普伦提斯镇
我们走出沼泽,返回城里。虽然头顶艳阳高照,我仍感觉世界一片黑暗。我们再次穿过田野,一路上就连麦奇也少言寡语。我的声流翻腾着,冒着泡泡,活像炉火上的一锅炖菜。直到我停下脚步,努力平复心情,声流才安静一些。
寂静这东西,世上绝无仅有。不仅这里没有,哪里都没有。甚至在你睡觉、独处的时候,寂静都不会存在,永远不可能存在。
我是陶德·休伊特,我闭上双眼,心中默想,我12岁零12个月大,我住在新世界的普伦提斯镇。再过整一个月,我就成年了。
这是本教给我的一个小诀窍,可以平息我的声流:只需闭上眼睛,尽可能保持清醒、保持平静,告诉自己“我是谁”。因为声流会使人迷茫,忘却自己的身份。
我是陶德·休伊特。
“陶德·休伊特。”麦奇在我旁边小声地自言自语。
我深吸一口气,睁开双眼。
这就是我的身份,我是陶德·休伊特。
我们继续前进,与沼泽和河流相背而行,爬上一片荒凉的山坡,走到城镇南侧一段不高的山脊处。这里是学校的旧址。学校的存在不仅短暂,而且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我出生前,妈妈们在家教育自己的儿子;后来,世界上只剩下了男孩和男人。于是,我们只好利用录像带和资料自学知识。再后来,普伦提斯镇长说它们“对学生的思想纪律有害”,禁用了这些教具。
普伦提斯镇长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。
因此,差不多每半年,哭丧着脸的罗亚尔先生就会召集全镇男孩,把他们带到这里,远离声流密集的镇中心。此举其实并没有多大效果,在一间装满了男孩声流的教室里,正常教学几乎是不可能的;要想进行任何类型的考试,也完全不可能,哪怕没有人作弊,更何况大家都想作弊。
然后,有一天,普伦提斯镇长决定烧掉所有书籍,每一本都烧掉,连家庭私人藏书也不放过,因为他认为书籍有害。罗亚尔先生本是个和蔼的老师,为了在学生面前保持严厉,他总是灌自己威士忌;后来他放弃了,找了把枪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我的学校生涯也就此结束。
本在家教授我其余课程,比如机械、备餐、缝纫和务农的常识等等。我还学了许多生存知识——如何打猎,如何识别可食用的水果,如何通过月亮方位判断方向,如何使用猎刀及猎枪,被蛇咬了之后如何救治,如何尽力平息自己的声流。
他还想教我读书写字。但是一天早晨,普伦提斯镇长从我的声流中发觉了此事,便把本关了一个星期。就这样,我没法继续学习书本知识和其他知识了,更何况每天还要去农场干活儿。从此,我的生活只剩下维持生存,读书能力则再也没有提高。
没关系,反正普伦提斯镇的人谁也没想着写书。
路过学校旧址之后,麦奇和我继续沿着不高的山脊上行,眺望北方,望到了我们所在的全镇。现在全镇规模已经不大了:一家商店(曾经有两家)、一家酒吧(过去是两家)、一间诊所、一座监狱、一座歇业的加油站、一栋镇长住的大房子、一个警察局,还有一座教堂。一条短小的马路贯穿镇中心,那是过去铺建的,日后并未得到妥善维护,很快就变成了碎石路。所有房子都荒凉破败,郊区坐落着几座农场,有的已经废弃,有的依然投入使用;有些农场已经空无一物,还有一些景况更为凄凉。
这就是普伦提斯镇的全貌。全镇只有147人,人口数量还在持续减少。总之,全镇共有146个成年男人和一个即将成年的男孩。
本说,以前新世界还有其他定居者。大约在我出生的十年之前,所有船只都在同一时间登陆。和斯帕克佬开战后,斯帕克佬放出病毒,其他定居者被灭族;普伦提斯镇也差点遭到清洗,多亏了普伦提斯镇长的军事能力,人们才幸免于难。虽然普伦提斯镇长本人就是一场噩梦,但至少在这一点上,我们得感谢他:因为他,我们才成了这个没有女人的空空荡荡的大世界里唯一幸存的族群。可这个世界并不怎么样——在这个仅剩146个男人的小城里,每过一天,人就少一点。
因为有些人无法接受现实,不是吗?他们像罗亚尔先生一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还有些家伙人间蒸发了,比如我们的老邻居高尔特先生,他之前经营着一座绵羊牧场;又如镇上第二好的木匠迈克尔先生;还有范维克先生,他儿子成年的当天,他就失踪了。这并不是什么怪事。如果你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失去未来、声流肆虐的小城,你也会想逃,即便无处可逃。
作为城里唯一的未成年男孩,我仰望小城,可以听到剩下那146个男人的动静。我能听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。他们的声流如同泛滥的洪水,如同燎原之火或苍穹一般庞大的怪兽,无情地向我扑来,而我无路可退。
此情此景如斯,每一天每一秒,我都在这个臭烘烘、蠢兮兮的城里过着我那臭烘烘、蠢兮兮的日子。别想堵上你的耳朵,没用的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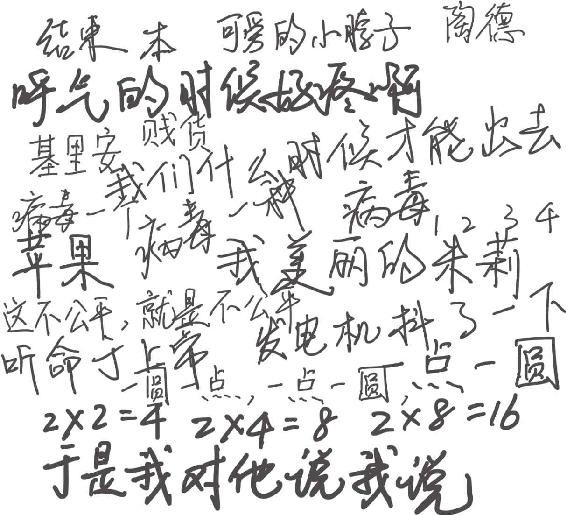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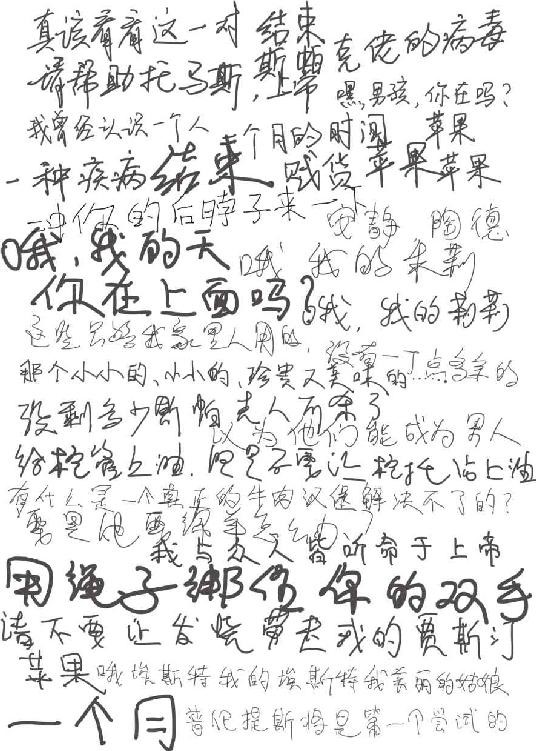
这不过是胡言乱语,人们聊天、抱怨、歌唱和哭泣的声音。此外还有画面,突然冲进你脑海的画面,不管你多么排斥,它们还是会涌进你的脑子——回忆、幻想、秘密、计划、谎言。即便大家都知道你在想什么,你还是可以在声流中撒谎,将一个想法藏到另一个想法底下,用平常的景象掩饰,只要别想得太清楚,或者努力往真实想法的反面想。然后谁都无法从声音的洪流中分辨出哪一股是真正的水,哪一股是骗人的。
人会撒谎,尤其是自欺欺人。
举例来说,我从未亲眼见过活生生的女人或斯帕克人。但是,我在录像带里见过他们——当然那时的录像带还不是违禁品,而且我总是在人们的声流中看见他们,因为男人们的脑子里除了女人就是敌人,还能有什么呢?可是声流中的斯帕克佬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凶,比录像带里的要厉害得多,不是吗?声流中的女人头发颜色越来越浅,胸越来越大,穿的也越来越少,比录像带里的更随便,也更热情。所以,有一件事要牢记,我要告诉你们这件顶顶重要的事,那就是声流并非真相,声流是人们渴望成真的想法,二者之间差别巨大,大到如果你不小心就会被它害死的程度。
“回家,陶德?”我腿边的麦奇大声叫了起来,因为它在声流中只能这样说话。
“是啊,我们回家。”我说。我们住在城中另一头,东北角,所以得穿过整个镇子才能到家。于是,我们快步前行。
我们首先路过的是菲尔普斯先生的商店。这小店快要倒闭了,就像整座小镇一样。菲尔普斯先生总是沉浸在绝望中。就连人们去他店里买东西,他尽可能礼貌地接待顾客时,那份绝望也会涌出来,将人包围,就像伤口溢出的脓水。结束了,他的声流说,一切都结束了。贱货、贱货、贱货,我的朱莉,我亲爱的,亲爱的朱莉。朱莉是他曾经的妻子,在菲尔普斯先生的声流中,她总是一丝不挂。
“你好,陶德。”我和麦奇匆匆走过时,他打了声招呼。
“你好,菲尔普斯先生。”
“今天天气不错,是吧?”
“确实如此,菲尔普斯先生。”
“不错!”麦奇叫道。菲尔普斯先生大笑,可他的声流一直在说“结束”,呈现出朱莉脱光的场景,还有他记忆中妻子的日常,就好像那有多特殊、多了不得似的。
我觉得,对菲尔普斯先生而言,我的声流没什么特别的,不过是些忍不住想的小事罢了。不过,我必须承认,我发现自己在不自觉地强化那些日常想法,以便掩饰在沼泽发现的那个洞,将它藏在更大的声流中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,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隐瞒此事。
可我就是隐瞒了。
麦奇和我继续快步前行,因为下一站就是加油站和哈马尔先生家。加油站已经歇业了,去年面世的裂变发电机淘汰了汽油。如今的加油站活像一截受伤的脚指头,又笨又丑。没人愿意住在加油站附近,除了哈马尔先生。哈马尔先生比菲尔普斯先生还过分,他会用声流向你咆哮。
他的声流丑陋而愤怒,还夹杂着包含你本人的画面,而且十分暴力血腥,你绝不会想看到。因此,你只能努力增强自己的声流,甚至将菲尔普斯先生的声流也裹挟进来,然后一股脑地全抛给哈马尔先生。苹果,结束,第一次高手击球,本,朱莉,真好,陶德?发电机抖了一下,脱光,闭嘴,给我闭嘴。突然我接收到一句:看着我,孩子。
尽管不想,但我还是不小心扭过头,向他望去。我看到哈马尔先生站在他家窗口,他正看着我。一个月,他想。他的声流中出现了一个画面,画面里是孤零零站着的我,显得比以往更孤独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也不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还是他精心设计的谎言。于是,我想象一把锤子不断砸向哈马尔先生的头,可他无动于衷,只是在窗口向我微笑。
前面的路绕过加油站,又到了鲍德温医生的诊所。那里聚集着许多无病呻吟的人,他们其实没什么毛病,但非要在医生面前又哭又闹。今天去看病的是福克斯先生,他说自己喘不上气。若他不是个老烟枪,倒还值得同情。途经诊所之后,全能的上帝啊,你又会看见那家蠢透了的酒吧:就算到了这个点儿,那里依然人声鼎沸。他们爱把音乐的音量开到最大,想借此掩盖声流。可总是适得其反,让人同时听到吵闹的音乐和同样吵闹的声流。更糟糕的是一群醉汉的声流,其冲击力堪比横空挥来的球棍。在这里鬼哭狼嚎的总是那几个人,他们絮叨着令人汗毛倒竖的陈年往事和世上已经绝迹的女人。他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女人,不过说的话都没什么逻辑。因为醉汉的声流和酒后胡话是一样的:含糊、无聊又危险。
经过镇中心时就更是寸步难行了,因为这里的声流太密集,你会感到肩上有千斤重量,压得你不知下一步该迈向何方。坦白说,我不知道人们该怎么做,我对接下来的日子一无所知,不知道成年之后该做些什么才能改变现状。
绕过酒吧,向右一转,就来到了警察局和监狱,二者建在一起,你根本想不到,这个小镇的居民会多么频繁地出入这两个地方。警长是小普伦提斯先生,他只比我大两岁,成年还没多久,但是工作上手很快,做得不错。他的号子里关着那些普伦提斯镇长每周吩咐他拘押的犯人,目的是杀鸡儆猴。现在里面关的是特纳先生,因为他没有“为了全城的利益”提供足够的玉米,其实就是没有向普伦提斯先生和他的手下上交免费的玉米。
现在我已经带着我的狗穿过了小城,将声流抛在身后,菲尔普斯先生、哈马尔先生、鲍德温医生、福克斯先生,酒吧里震耳欲聋的声流,小普伦提斯先生的声流,特纳先生呻吟的声流,这些都过去了,但还没完,接下来是教堂。
当然了,教堂是我们来新世界的最初缘由。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听到阿隆布道,他会讲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充满腐败和罪恶的旧世界,我们又是怎样发奋,在全新的伊甸园中开始了纯洁友爱的新生活。
这一套挺管用,是吧?
人们依然去教堂,因为他们不得不去,尽管镇长本人并不怎么去,只留下我们其余的人听阿隆讲:我们在这里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彼此,就是大家伙儿,所有人都要在这个集体中团结。
他还会讲,一人沉沦,万人俱灭。
他老是说这句话。
麦奇和我尽可能安静地从教堂门前走过。祈祷的声流从里面传出来,带来一种特殊的感觉——疯狂而病态,就像人们争相将自己耗尽。尽管他们的祈祷都是老一套,但还是不断有泣血的感觉。上帝,求求您,帮助我们,拯救我们,原谅我们,帮助我们,拯救我们,原谅我们,把我们救出去吧。上帝,求求您了。上帝,求求您了。不过,据我所知,还没人听到上帝这位老兄的回应声流。
阿隆也在教堂里,他刚刚散步回来,正在面向信众布道。除了其他的声流,我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。他说的都是牺牲、《圣经》、赐福、圣徒之类的内容。他喋喋不休,声流像灰色的火焰,一片混沌,你无法从中清晰地辨别出什么。他很可能有什么阴谋,不是吗?他布道可能是为了掩饰,我已经开始琢磨他到底在掩饰什么了。
然后,我听到他的声流中出现了“小陶德”。于是我赶紧说:“麦奇,快走。”我们一路小跑,离开了教堂。
我们爬上普伦提斯镇的山,经过最后一栋建筑——镇长的宅邸,这里有全镇最古怪、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声流,因为普伦提斯镇长……
这么说吧,普伦提斯镇长与众不同。
他的声流清楚得吓人,我说“吓人”是真吓人。他坚信可以让声流遵守规矩。他坚信人可以让声流变得整齐有序,如果你可以管理声流,你就能好好利用它。当你经过镇长的宅邸,你就能听到他的声音,听到他和他的亲信的想法。他们一直在做思考练习——数数,想象完美的形状,整齐划一地念念有词,比如我即方圆,方圆即我,也不知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。他好像在组织一支小小的军队,为某些事情做着准备,又像是在打造一件声流武器。
这像是威胁,像是变化的世界要将你甩在身后。
12344321。我即方圆,方圆即我。12344321。一人沉沦,万人俱灭。
我即将成年,而成年男人是不会落荒而逃的。但我还是催促麦奇加快步伐,尽可能远远地绕开镇长宅邸,踏上通往我们家的碎石路。
过了一会儿,我们回头已经看不到小城了,声流的动静渐渐弱了(尽管永远不可能消失),我俩终于能顺畅地呼吸了。
麦奇吠道:“声流,陶德。”
“是啊。”我说。
“沼泽安静,陶德。”麦奇说,“安静,安静,安静。”
“是的。”说完我略加思索,赶紧说,“闭嘴,麦奇。”然后我拍了一下它的屁股。它说:“哎哟,陶德。”我回头望着城镇的方向,声流一旦传出去,就没办法半路截住。如果这股声流是带画面的,随风飘动,不知道你是否会看到一个洞正飘离我的身体,飘离想守护这个秘密的我。这只是一小股声流,夹在其他喧嚣的声流中很容易被忽略,但是它产生了,传播了,飘走了。它正朝着有人的世界飘去。